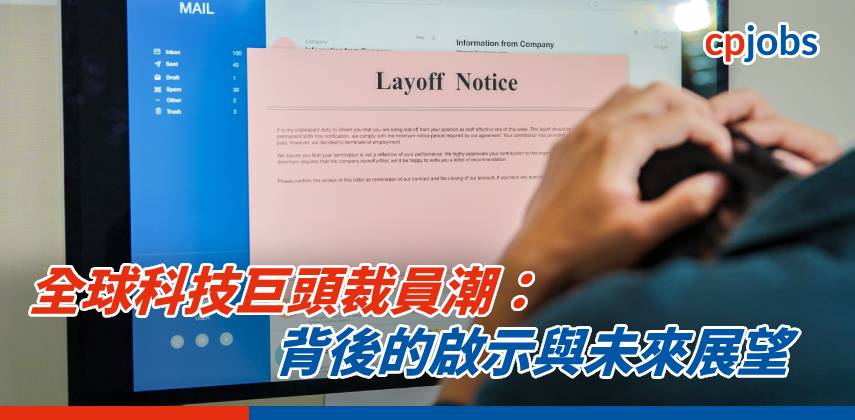近日, 香港爆發的「藥倍安心」(Medisafe)爭議事件, 再次將「吹哨者」(whistleblower)的角色推上風口浪尖。這宗事件源於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四學生潘浠淳聲稱自行研發的人工智慧醫療平台「藥倍安心」, 憑此奪得多項本地及國際創科獎項; 然而,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鄭曦琳(Hailey)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質疑潘同學涉嫌「請槍」——即委託美國公司AI Health Studio開發平台, 而非原創作品。鄭曦琳的揭發引發廣泛討論, 但隨之而來的是她遭受嚴重滋擾, 包括身份被盜用、被誣衊為性工作者, 甚至有人身安全威脅。這不僅暴露了學術誠信問題, 更凸顯了吹哨者在揭露不當行為時所面臨的風險與缺乏保障。本文將以此事件為切入點, 探討吹哨者法例及保障, 加入多宗著名案例(如Enron財務醜聞及太空梭爆炸事件), 並分析其道德價值及重要性。
吹哨者是指在組織內部或外部發現違法、不道德或危害公眾利益的行為, 並主動揭露的人士。他們往往是公司員工、政府官員或專業人士, 透過舉報來防止更大損害; 吹哨者經常面臨報復, 如解僱、法律訴訟、社交孤立甚至生命威脅。因此, 許多國家已立法提供保護。
在全球範圍內, 美國的《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1989)是經典範例, 保障聯邦員工免受報復, 並提供保密及補償機制。歐盟的《吹哨者保護指令》(EU Whistleblower Directive, 2019)要求成員國建立舉報渠道, 涵蓋公私部門。台灣於2025年7月22日正式施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提供工作權保障、身分保密、人身安全保護及責任減免四大機制, 舉證責任倒置, 讓揭弊者無後顧之憂。
反觀香港, 吹哨者保障相對薄弱。目前並無專門法例, 僅靠零散條文如《僱傭條例》禁止僱主因員工作供而解僱, 或《防止賄賂條例》保密舉報者身份, 但這些規定不足以涵蓋全面報復, 例如社交媒體滋擾或私人報復。多年來, 立法會議員及民間團體呼籲制定專法, 例如參考國際標準, 設立獨立舉報機構及反報復罰則。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曾指出, 若吹哨人不受保障, 公眾知情權及利益亦難以維護。在「藥倍安心」事件中, 鄭曦琳作為吹哨者, 雖揭露了可能涉及的學術欺詐及資源分配不公, 但卻面臨身份盜用及誹謗, 凸顯香港法例的空白。
吹哨者的貢獻往往改變歷史, 以下是幾宗全球及本地相關案例, 展示他們的勇氣與代價:
愛德華·史諾登(美國,2013):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史諾登, 揭露NSA大規模監控計劃, 包括竊聽全球通訊。他從香港逃亡至俄羅斯尋求庇護, 至今流亡海外。美國政府以間諜罪起訴他, 但他的揭發促使全球隱私法改革, 如歐盟GDPR。此案凸顯吹哨者往往面臨國家級追捕, 道德價值在於捍衛公民權利, 對抗權力濫用。
雪倫·沃特金斯(美國,2001,Enron財務醜聞):安然公司(Enron)前副總裁沃特金斯, 向CEO揭露公司財務欺詐, 包括隱瞞巨額債務及虛假盈利報告。這導致安然倒閉, 高層如CEO Jeffrey Skilling及主席Kenneth Lay入獄, 數千員工失業及養老金蒸發。此案暴露企業貪腐, 促使美國通過《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加強吹哨者保護及財務披露要求。沃特金斯雖面臨職場孤立及威脅, 但她的行動保護了投資者, 體現了企業倫理的重要性。Enron事件被視為美國史上最大企業欺詐案, 損失達740億美元, 凸顯吹哨者如何防止系統性崩潰。
羅傑·布瓦喬利與艾倫·麥當勞(美國,1986,太空梭挑戰者號爆炸):在太空梭挑戰者號(Challenger)發射前, 工程師羅傑·布瓦喬利(Roger Boisjoly)及艾倫·麥當勞(Allan McDonald)等吹哨者, 警告低溫會導致O型環密封失效 ,可能引發爆炸。他們向NASA及僱主Morton Thiokol高層提出異議, 甚至拒絕簽署發射許可, 但警告被忽視, 挑戰者號發射後73秒爆炸, 7名太空人喪生, 包括教師Christa McAuliffe。此案導致NASA改革安全文化, 強調聽取工程師意見。布瓦喬利後來成為道德工程的倡導者, 但面臨職場報復及心理創傷。這起悲劇凸顯組織文化忽略吹哨者警告的後果, 道德上強調安全優先於進度。
吹哨者的道德價值在於勇氣與正義。他們秉持「義不容辭」的原則, 犧牲個人利益換取社會福祉, 體現了康德哲學中的「道德義務」——不因後果而行動, 只因正確。從儒家視角, 這類似「君子不黨」的精神, 拒絕同流合污。
吹哨者行為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 首先促進透明與問責, 吹哨者如「社會哨兵」, 及早揭露問題, 避免更大災難, 如Enron案若早獲重視, 可避免投資者巨額損失; 或挑戰者號事件, 若聽從警告, 可挽救7條生命。其次, 遏止腐敗與不公, 在企業或政府, 內部監督往往失效, 吹哨者填補空白, 推動改革, 如史諾登案改變全球隱私標準。再者能夠提升公眾利益, 無論是環境污染(如《黑水風暴》電影中揭露化學毒物)、財務欺詐或學術造假, 吹哨者保護弱勢群體, 維護社會公平。
然而, 缺乏保障會抑制揭露意欲。研究顯示逾70%潛在吹哨者因恐懼報復而沉默。這不僅損害道德風氣, 還放大系統性風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若不立法保護吹哨者, 將影響投資者信心及創新生態。
總括而言,「藥倍安心」請槍事件提醒我們, 吹哨者如鄭曦琳的勇氣值得讚揚, 但她遭受的滋擾暴露了香港法例的不足。參考全球案例如Enron及太空梭爆炸, 香港應盡快制定專門條例, 提供全面保障, 包括保密、反報復及補償機制。只有這樣才能鼓勵更多人吹響哨子, 守護公義與透明。畢竟一個健康社會, 需要每位公民的道德勇氣與制度後盾。